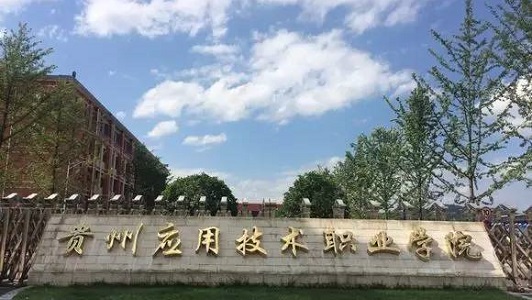创新教育,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STEAM、PBL、现象教学法......随着一个个新概念落地本土而渐渐被拉下神坛,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在“未来”、“变革”这些名词前踟蹰起来。教育,真的需要朝着新世界高歌猛进吗?
“做创新教育,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去考虑它新不新。很多时候,那是教育者对自己的一种绑架。”讲出这句话,任竹晞已经从事创新教育整十年了。

任竹晞“一出学社”社长创始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最早,带着对自己教育经历的反思与遗憾,任竹晞渴望给“精英学生”们更广阔的视野,或从教师这一侧突破,把教育从单一评价体系解绑出来,但收效甚微,老师学生们似乎并不那么需要新方法、新技术;
后来,得到机会进入某公立学校做“全人教育中心”,因与学校的“主流价值观”不符,这群履历光鲜的教育创新者又第一次尝到“被炒鱿鱼”的滋味;
2019年,任竹晞和她的团队终于找到一个走得通的模式,为那些被贴上“问题学生”标签的学生辟出了一个可以喘口气的地方,“一出学社”就此成立。

图注:“一出学社”老师团队集体照
故事并不复杂,对这个创新教育团队而言,“很多事都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样的情节,有了人的情感作注脚,进退之间,就不再像如水过无痕了。十年来,任竹晞始终坚持着初心,想让教育往前更进一步,可面对“进与退”这道命题,她却说,“某种程度上说,我也在‘退’,退出了自己的执念,退出了柳暗花明的感觉。”
一堵墙
“所谓最好的教育,也从没教我们认识自己”
2011年,任竹晞自美国归来,回国创办“一初教育”(一出学社的前身),希望通过实践式、项目式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在丰富的学习体验中找到兴趣和方向。
这一想法得到另一位合伙人的吴霞的响应。一拍即合的默契,来源于两位回溯成长过程中同样的遗憾。
任竹晞的教育经历,可称得上国内“学霸”学生的范式。高中就读于人大附中,赢在高考后,顺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从北京实验中学升入北京大学读金融的吴霞也是这样,最高学府、热门专业,几乎是国内“最好的教育”了。
“可是最好的教育,也从没教过我们怎么认识自己。”任竹晞无奈地笑了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可笑的,也很痛。我们当初的选择,都是因为‘不能浪费了这么高的分数’,从没想过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两位“学霸”创始人因而开始了帮中国“精英学生”发现自我的旅程。可实践却并不顺利,任竹晞很快发现,这种尝试对学生产生的实际效用小得惊人。“我们的项目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给了学生们一些体验,却很难触及根本。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学校,那套价值观太强大了。”
任竹晞曾碰到过一个成绩很优秀的孩子,但在项目中却表现得差强人意,因为总是拒绝合作。这个学生对她说,“我和我的手机就是一个团队,我不需要听别人怎么说。”跟别的孩子聊天,也只是问同学“考了多少分?排多少名?”争夺分数的游戏无可避免地导向了只剩竞争的同侪关系。通过单点突破式的学生项目去松动这种价值观,难度可想而知。

图注:学社日常-零废弃圣诞节
于是方向从学生扩展到教师。任竹晞想,当教师发生变化,学校课堂或许也能成为创新的一环,从而进一步促进教育氛围的变化。然而,这一想法得到的反馈,让任竹晞再一次领略到了变革的艰难。
任竹晞带着团队到学校里去给老师们做PBL等教学法的培训,最多的反馈竟然是“学这些能帮我改作业、批试卷更快吗?”、“明天高三就开学了,我为什么今天还在这里?”、“这是做课外实践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教主科的。”这并不难理解,对教师来说,影响教职KPI和未来发展的都不在这里。
比起沮丧,任竹晞更多的感受是“困惑”。“我们是不是从不缺少创新理念?为什么一到学校系统里,这些创新的理念、方法就落不下去?”
一道墙横亘在眼前,绕不过,敲不开,到墙那边去探个究竟成了唯一解。
一次实验
“我们成了问题学生的同伙”
恰逢其时,某公立学校希望做出一些创新教育的突破,便邀请“一初”团队进校实践,用“全人教育中心”来做一次实验。
所谓“全人”,即首先将学生当作一个真实的人去看待,而不是只以成绩论长短。这与任竹晞一贯的教育主张高度契合,看起来,这是一次互通有无的合作,还能让团队离一线、真实的教育场景更近,问题的症结或许也能看得更清楚。
事实上,这段经历的确带给任竹晞许多新的思考和启发。
“原来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学校里还有那么多学不进去的学生。”据任竹晞观察,1/3的学生学习困难,根本跟不上课堂节奏。还有1/3的学生在“假学习”,“看上去很正常,上课也听,作业也写,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
当这些学生的表现差到被老师停课,他们就会被安排到“全人教育中心”来。团队过去对“精英学生”的专业技术、方法一时间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从重新了解学生开始。
倾听学生和让渡主动权的动作,让任竹晞意外地发现,或许学生们最需要的真的不是“新东西”。学生们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学科成绩还是人际关系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可是“我们只是跟他们聊天、谈心,组织他们结成小组学习,没有用到任何花哨的新东西去教他们。”

图注:由学生发起的英语配音小组
这无疑对这群创新者的既有观念造成了冲击,“过去我们总觉得自己看得多、懂得多,别人不接受是因为他们不懂,可我们真的对他们足够共情了吗?我们真的看到他们需要什么了吗?”
正当新知在重塑教育理解时,整个团队却被学校“扫地出门”了。而此时距离受邀进校,才三个月。校方对任竹晞并不讳言,原本希望这里对被“停课”的学生来说,意味着一种惩戒,短暂的思想教育后要以更“端正”的态度回去上课。然而,学生渐渐喜欢上待在这个“全人教育中心”,甚至比在常规课堂上学得更好。
“在学校眼里,我们成了问题学生的同伙。”这一次的打击,远比之前来的剧烈。任竹晞坦诚,那是她从事创新教育后第一次有“退”的想法,“就是很悲观,在想是不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是不是应该放弃......”
一出学社
“我们决定信任对方”
“可是你知道吗?”任竹晞动情而真诚地讲述着,“当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就很难装模做样再去做一些流于表面的事了。”
任竹晞及其合伙人吴霞,连同整个创始团队成员,都各自手握一张漂亮的简历,转身去做光鲜体面的工作,或许才是更符合世俗价值判断的职业规划。但任竹晞似乎并不把那条“未选择的路”看作一种诱惑,相反的,在她当时的心境里,如果就此放弃,那些她一直试图改变的问题,非但没有改变,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想到那群“被放弃的孩子”,这支年轻的队伍仍然“意难平”。
2019年,“一出学社”正式成立,定位为专门为“问题学生”打造的成长中心。“一出”全人导师、招生负责人黄丹纠正我,可不可以改为“困境学生”——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只是被困住了。
在教学一线的见闻让任竹晞感受到,“困境学生”绝大部分受困于周围的不信任,老师、同学,甚至家长,都觉得他们“不配”:不配接受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教学体验。
于是,“一出”给出的应对策略也与之前截然不同了。当然,更加灵活开放的课堂教学是标配,只是核心远不在这些教学手段了。大道至简,“一出”教育的关键,唯有“信任”二字。

图注:学社日常-新年活动
“一出”给学生的自由度大到惊人:一个面向12-18岁学生的全日制成长中心,没有必修课,所有课程均为选修;对学生最基础的学分要求是一季度修够5个学分,也就是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对学生行为的管理只有三条硬性规定:遵纪守法、不影响他人,不危害学社,在此基础上,作息、打游戏等都由学生自主管理,不受学社干涉。
或是两位创始人的个人风格为这里营造了温柔而坚定的文化,或是团队在教育探索路上愈发信奉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产生影响。在常规视角的不可思议中,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而且,真的奏效了。
一个曾经从重庆市某重点中学休学的男孩儿,学不进去、人际关系也一团糟,跟老师、父母也只剩争吵。然而在“一出”待了一年后,却顺利地恢复了学业,也开始打开心扉交朋友,整个人的状态都比任竹晞初见他时开阔了许多。
“所以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呢?”我问。
任竹晞回忆,这个孩子在学社里也并没有选几门课,还是每天就做自己的事。“但我想,他感受到了信任。很多孩子最初都不相信我们真的信任他们,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下意识地反抗一切大人的安排。”而当决定权真的交回孩子自己,他们会意识到,自由也是一种责任。
采访后,我曾短暂想到过杨永信,那个用电棍制服了“问题学生”的“家长救星”。但随即意识到,完全站在对立面的“一出”是如何做出本质改变的:他们从不试图“改造”学生回归“标准”,而是把标尺交给了学生自己。
一条路
“我们一起走出教育的困境”
在教育创新的这条路上,任竹晞终于用“一出”这个产品打通了平衡教育初心和商业运营的难点。
但走心与标准化间的掣肘,仍然存在。在任竹晞地设想中,“一出”或许在未来会多开几家成长中心,但永远无法工业化地拓展下去。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整个创新教育行业的一个小小缩影。回归教育本质的全新生态,需要新的环境、新的关系、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共同打造,学生才能切实感受到成长的安全感。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把蛋糕做大”,因而成为创新者们的共同期待。只是跟那种跑马圈地式的“做大”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希望更多有理念、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
在任竹晞的十年里,她遇到许多同行前辈的支持。“一土教育”成为“一出”的天使投资人,前者创始人华章也曾在运营管理方面给“一出”团队许多中肯的建议;成都先锋学校的校长刘晓伟也讲过一些极具前瞻性、令任竹晞回味隽永的观点:“我们的学校没有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如果有,那也是我的,不是学生的。我怎么可以用自己的规划去绑架学生呢?”
前辈们对她来说,更像是“同行者”,他们互相照亮,给予支持。如今,任竹晞也已然成为创新教育这条路上的“先行者”了。

图注:学生作品-零废弃圣诞树
“如果有后辈也希望加入进来,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我问。
“首先就是放下执念,不要去考虑你做的事情新不新。做教育,不是因为办学者而特别,要为了学生而不同。”任竹晞接着说,“还有,照顾好自己。”
在《我不幸福,那天我想放弃了......》一文中,任竹晞曾坦诚这份理想职业是如何将自己一步步消耗到濒临崩溃的,“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和学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通的,比如,如何面对自己的软肋?”
在传统的教育语境下,教师的第一关键词永远是专业,但在任竹晞看来,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老师的不幸福,一点儿也不比学生的少。“可只有老师做到‘全人’,才有可能用‘全人’的眼光看待孩子。这对从事教育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两个小时讲完十年的故事,我仍能从中觉察到任竹晞的变化。她永远有理想,也永远有困惑,也似乎准备好下一次被打破、重塑。任竹晞引用了她钟爱的物理学家费曼的人生哲学,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想?如果及时改变能离真相更近,为什么要为放弃之前的坚持而懊恼?
“每个孩子真的都有无限潜能吗?”、“我们给孩子的行为表现评分,可是评分又代表什么呢?”、“标准化与走心之间的最优平衡点到底在哪里?”还是有许多问题语焉不详,但是没关系,“世界会慢慢清晰可见,我和我重新携手前行。”(引自陆忆敏《路遇》)
采访&撰文:张楠
主编:吴慧雯
运营总监:达文姣
编辑&运营:李燕妮
视觉:聂谭杰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