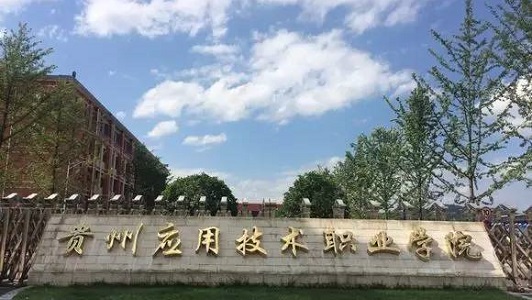一、律法与良知:重视校企合作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我国长期以来大受追捧?因为它树立了校企双元密切合作的典范。为什么我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难以做到“德国成效”?有人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建立在严格的《职业教育法》基础上。可是,我国不少地方也出台了校企合作条例和产教融合政策(2008年12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专项法规),为什么在实践中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有效性不如德国“双元制”呢?我认为,提高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必须把律法建设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
现代职业教育起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因此当职业教育随着工业化而向全球辐射的时候,就天生地带有欧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比如,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具有严格的“资质文化”,这种文化源于德国传统行会制度,它要求劳工、企业、学校和政府进行密切而持续地合作。即使与德国文化有紧密互动的美国职业教育,由于缺乏德国行会文化传统,也很难在劳工、企业、学校和政府之间做到德国那样的密切合作的成效。同样,根植于农业经济模式的中国儒家文化则似乎与现代职业教育格格不入,比如缺乏强大的行会传统和刚性的契约精神等等,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在西方很有效用的“校企合作协议”在我们这里却滞留于纸面上。但是,中国儒家文化却有进取、灵活、包容、责任、信任、致良知等等特质,这种特质始终潜在地影响着我们的职业教育实践。我发现,凡是具有这些文化特质并且在“校企合作”中善用之的教师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我访谈了一些就业质量高的职业教育教师,他们在“校企合作”方式上与别人并无不同,但是他们无一不是事业进取者、意义发现者、灵性启迪者和责任担当者,他们“立心而致用”,不仅善于激发学生潜能,而且善于挖掘市场需求,他们和用人单位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关系,一些用人单位宁可放弃本科生也愿意选择他们的“高职生”。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写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支持社会力量、民间资金参与举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参与办学的举办者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这里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都是建立校企深度合作关系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院校和企业在合作中浅尝辄止,他们将某些领域列为“红线”,比如校企在共建职业院校、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方面的收益和资源损耗如何计算,特别是国有资源的损耗如何计算,这些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所以合作一旦触及“红线”即刻“内卷”,出现所谓“合作协议轰轰烈烈,协议落地冷冷清清”的现象。因此,提高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重视法律法规建设是一个方面,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是“致良知”,即在研究我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律法与良知的统一。当年,陶行知先生进行了很好的中国职业教育实践,他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但是他并未照搬杜威理论,而是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工业现实把杜威理论“翻了半个筋斗”,他主张在中国“必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由此创造了“学校即社会”“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等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中国学派”。应当说,陶行知是把现代实用主义和中国传统心学理论相结合的典范。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根本是“致良知”,或者说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我们认为,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中的“致良知”就是“去名”“除利”“挖潜能”“戒浮躁”“有温度”,坚持“长期主义”。由于“教育市场是一个依赖政策干预的计划经济市场”,如果没有教育工作者的“致良知”,如果“舍心逐物”而不“立心致用”,那么与市场经济的合作就会出问题。因此,校企合作中的“致良知”首先是学校教师的“致良知”,比如主动对接中小微企业,担负责任。

二、校企与需求:建立职业院校和大中小微企业的大数据平台

有需求才有合作,合作是为了满足需求,否则就成了形式主义。当然,满足什么需求也是一个问题,是人才需求还是名利需求?如今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很多,不少单位和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解决了有效性问题,甚至认为他们建立了“高起点、高平台、高集成的校企合作新型办学形态”,这是“为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走向世界贡献智慧”。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校企合作模式都停留在为什么做和怎么做层面,并没有完整的效度检测结果及其研究。本文认为,寻找解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的“瓶颈”问题的必要办法是,从需求和信任的逻辑前提出发,引入第三方大数据平台。为此,职业教育工作者必须在理念上有一个转变:从精英主义职业教育向大众文化的职业教育转变;从封闭性职业教育向开放性职业教育转变;从输出型职业教育向需求型职业教育转变;从学校职业教育向“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转变”;从“就业专业技能”向“美好生活技能”转变;从重视文凭教育向文凭与证书并重转变。从新理念出发,我们可以建立职业院校和大中小微企业的大数据平台,链接学生、学校、企业、政府、人力资源公司五个相关方,一键搜索即可找到和建立需求连接。建议这种大数据平台是由国资委控股、民营企业负责运营的第三方平台。平台功能是:整合全国中高职学校和大中小微企业资料,动态发布需求信息,提供合作源、合作需求和信息评估服务,对校企合作进行分类分层管理;聘请教育学家、经济学家、法律顾问和其他技术专家,解决谈判事务、合作纠纷、法律事务、财务事宜、监督落实,以及合作交易机制,提供税收担保、利益分配机制等等;解决校企合作的考核评价机制,评价结果由评价方和被评价方共同管理。平台技术是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算法对双方利益进行确权,一旦在区块链上确权,双方的后续合作都会被实时记录,而且可追溯、可追踪、可审计,可信度和透明度也高。总之,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使校企双方只专注于内容合作,一切服务交给平台。

三、初心与使命:关注底层大众的职业生活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有句名言: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职业教育也是一样,当我们骑着工具主义的战马驰骋畋猎的时候,应当感受到令人心发狂的喧嚣;当我们醉心于市场需求和专注于就业技能的时候,也需要问一问学习者的职业志趣与天赋才能在哪里。实践证明,职业教育并不是解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灵丹妙药,始终把有生命的职业教育捆绑在经济效率的战车上一起狂奔,恐怕职业教育有心无力。虽然职业教育离市场很近,甚至被称为“零距离”,但是发展职业教育不能浮躁,因为企业不能浮躁,市场也不能浮躁。浮躁是一种疾病。如果我们看到职业教育不关心人而关心物、不关心内在而关心外界、不关心启迪而关心融入、不关心解放而关心规训,职业教育就患有“浮躁病”。澳大利亚教育学家比利特说:“职业教育的病痛是,虽然能够激发个人潜力、具有社会解放作用,却常常被忽视。”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